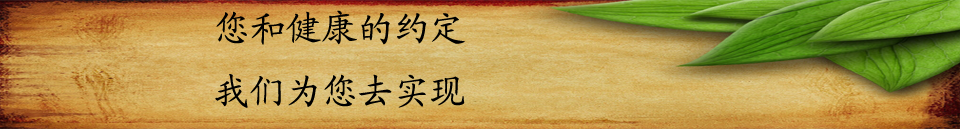
跨界经纬学术陈少华进退维艰的底层写作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与我们及时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进退维艰的底层写作
——余华小说创作心理的整体观
陈少华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6期
余华底层书写初始冷峻继而温润,至晚近两者的混搭,越过关于冷暖的线性描述,实则统摄于作家“实际上没什么变化”的心理底色以及喜剧性的审美心理。写作的驱力与依赖、死而复活的宣泄方式、作为症候所表征被抑制的羞愧,整体揭示出余华的底层创作心理的意蕴,不妨用斯宾诺莎的名言加以概括:“毋憎恶,毋嘲笑,毋惋惜,唯求理解”。心态;喜剧性;羞愧;整体观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一般而言,我认为每个作家都只在写一本书,尽管这本书有许多卷。”这一说法同样适合用来概括余华。尽管余华对底层的诸多写作各有侧重和变化,总体上他的写作也应当看作关于底层的一本书。余华在其创作过程中多有侧重,但关于底层的认识仍然统摄在一种作家自我的整体把握中,以相对的一致性抑制可能的歧义性。在一次关于自己前后期作品认识的对谈中,余华认为自己的作品从思考的本质和对人的理解来看,“实际上没什么变化”①。因此,从整体上对作家写作的精神现象加以辨析,才能越过线性描述,把握统摄作家的精神实质。尤其是,对折射作家精神现象之创作心理的探讨也宜进行整体上的阅读,以探求余华小说之于他的写作对象,其创作心理呈现怎样的底色、审美以及伦理判断。整体把握即意味着不再去划定非此即彼、前期后期、显性隐性以至混沌的作家精神与情感,而是在作家写作的驱力、趣味以及价值呈现的方面进行相关探究,以期阐明作家真实存在却被忽视或被遮蔽的精神状态。
余华
一、底层之奇:写作的驱力与依赖
从现代文学来看,余华对于底层的写作,有延续,同时也有断裂,且断裂要大于延续。延续的判定,是来自与鲁迅等作家相联系的文学传统的认识。对于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而言,有关国民性改造的表达,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个体觉悟的同时成为社会批判的共识。在80年代的先锋作家中,与孙甘露的语言试验、格非的非现实的个体乌托邦、马原的叙述圈套等试验不同,余华的作品一开始就以不同凡响的形式去表达对群体特点的认识与批判,这样就很容易让人把余华与鲁迅联系起来。余华小说对人之麻木、愚昧、残忍的存在状况的揭露,尤其能够得到那些了解启蒙文学来路以及诉求的读者的认同。此为余华对乡土人物书写延续的证明。现代文学中写小人物的另外一极是沈从文。正像沈从文写船夫、农民、小工业者、士兵等在社会边缘游走的底层人物一样,余华也同样写到农民(《活着》中的福贵)、在乡镇之间游走的送蚕蛹的游民(《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城市打工的各色人等(《第七天》中的鼠妹等),这也是对小人物书写的延续。但断裂是更鲜明的,甚至可以说开创性地描写了底层的景观。与沈从文写了萧萧、翠翠的质朴不一样,余华的底层人物并不是单纯地表现质朴。福贵质朴吗?在忍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以及亲人的离去后仍乐呵呵活着,他靠的是和他一道存活下来的那头牛一样的存活之道。这可能是幸福与残忍的底层风景。与鲁迅写作乡土的气息不一样,余华对人物行为的叙述显得机械与无奈。更为突兀的地方,则体现在余华的小说从来没有我们关于阅读乡土小说习惯看到的背景描写,没有自然的风光、没有民俗的暖热、没有田园江河的旖旎——这些在底层人生存的世界中,已然成为抚慰人物生存、寄托作者情意的文学本体世界,构成作家询问世界、探索城市生活、对话城市文明的媒介。余华的底层变成没有记忆、没有来路、没有田园风景相伴的“新”人类。断裂的底层写作映衬着现代社会造成的蛮荒。对风景的侵蚀与掠夺,对记忆的模糊,正是余华所描绘的底层人“新”人类的境遇。底层人无所依靠、四处漫溢,化成关于自我的背景,也是自己吞噬自己的背景。余华写作底层人带出的震撼晕眩感长久地支配着作家的写作。在早期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给“我”的成长(同时也是给读者)造成极大震撼的是那些暴抢苹果的人,也包括合谋的运苹果的卡车司机。这些并未被特别聚焦的群体既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一类人;作为小说的氛围构成,实际上也是小说的一个主题。对于这篇小说,从“我”的认识来说,与其说荒诞构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不如说是对这一群人“奇异”行为的书写带出了荒诞感。实际上,纵观余华的创作,作家有关这一底层的认知主要还是奇异、奇怪、奇特的感觉,具有不可思议的能指。这种认知大概和奇巧无关,而是和某种蛮力以及这种蛮力转化而来的坚忍的体认有关。从作家三十多年的写作来看,有时候,他会被这种体认激怒,不知所措。有时候,他被相关力量的毁灭性、破坏性所震慑,却又要保持他独有的对峙;这种时候,他以冷漠的叙事来表达。有时候,相反地,他又会被生命某种随波逐流、以顺从表现执拗的坚忍所震撼而嘘唏不已,这种时候他就多以温情的叙事来呈现。在前期的写作中,余华把作为背景或氛围营造的底层人群从远景推向前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移至前台的人物,如代表作《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山峰,虽各有其名,但仍然是底层的抽象符号。他们的面目依旧模糊不清,他们的内心和情感也是空缺的。在这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哭泣与沉默也变成某种孤立的现象,然而他们的行动(暴力)却显得干脆,人物对死亡的到来以及死亡可能带来的恐惧浑然不觉。小说结尾有关山岗的器官摘除,因睾丸移植成功,给人卷土重来的感觉。相对这种前期的对人物的否定式写作心态,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则变成对人物的趋同认可。福贵和许三观不仅面目清晰,他们的自我意识也与行动吻合。对福贵来说,尽可能活着即是一切,不管是像畜牲还是像一株植物。不走向内心,不伤怀过往,不计较周围接二连三的死亡,只要活着——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福贵做到了,这难道不奇特吗?岂止奇特,简直就是奇迹。同样奇特的是,许三观对于生活给他造成的所有损失与伤害的接受,都是靠他特有的平衡来做到的,平衡之后也不会留下什么创伤。对应余华的写作过程,本人曾撰文从余华小说死亡书写的变化论及余华创作精神现象的变化特征①,其中提及余华在所谓后期的作品里,小说人物的死亡似乎得到了控制。然而,到《第七天》的出版,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作家变得踌躇起来:余华写底层的世界,一方面同时表达了冷漠与温情,另一方面对这两者的表现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犹豫——进退失据、左右为难,既在事件的新闻与虚构之间,也在对人物的愤怒与悲悯之间。这也许真实地揭示了作家对底层的心态,从而制约着作家的激情。当底层这样的写作对象已经无以出奇的时候,在思想上既难有突破,感情上也显得困乏。《第七天》的出版从两个方面印证着作家的精神结构:一方面是底层带给作家的驱动仍然绵绵不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前后期的划分,所谓冷漠到温情这样一种线性的创作心理只是表象。余华与底层的纠缠,成为作家创作的驱力与依赖。二、喜剧性/呕吐物、死亡与宣泄
余华在年曾说,《活着》发表22年了,至今“哪怕是朗读其中的片段,每读一遍,我都会哭一遍”③。对于作家寄托了强烈情感的小说,他的叙述通常会避免可笑性;在讲述人物遭遇的苦难时,通常也倾向于将世界赋予悲剧性的表达。余华小说创作心理中所呈现的绝望、灰色的调子也与此相关,并得到读者更多的认同。然而,针对有人对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认为《兄弟》《第七天》过于绝望的说法,余华则强调:“我的所有的小说都是光明的。”④显然,作家希望读者看到他小说创作的精神指向,希望给人积极温暖的基调。这不能不涉及余华对世界阅读的整体审美倾向和对底层人物叙述的审美心理,由此决定着他“光明的”写作形态,决定着他对黑暗污秽的呈现与遮掩。首先,余华小说的审美倾向与其说是悲剧性,不如说是喜剧性的。在对小说世界的把握中,余华把荒谬、不协调、错位、怪异、滑稽等富于喜剧性语义内涵的东西呈现给读者。所有早期的作品,从《十八岁出门》开始,《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无不体现喜剧性特征。在《鲜血梅花》中,20岁的阮海阔为父复仇却陷入人生命运的荒诞之中。可以想象,父亲仇人早已被他人所杀的事实决定阮海阔复仇漫游的喜剧性。《河边的错误》叙说疯子杀人和动机缺失的荒谬感。而在《古典爱情》中,大饥荒的恐怖与爱情执守方式纠缠一起,同样给人不协调的荒诞感。因此,余华在情节的演绎上多体现为喜剧性的死而复活的形态。余华因底层之奇的震撼,带出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一种喜剧性的死而复活的心理图式加以呈现,这是一种对事物开放的创作心理,是一种对应四季更替、生生不息的生命态度。死而复活的心理图式包括所有的对善恶事物的认识——原以为可以结束的丑陋邪恶以一种隐喻象征的方式浮出。正如《现实一种》的结尾,山岗虽然被枪毙了,但他的“种子”还在,给人些许恐惧,但更多的是喜剧性的滑稽感受;原以为悲戚生命的无常消逝却有幸存者福贵的活着,舒缓绝望的同时也让人看到希望。余华以他独到的方式表明,在有关底层的地平线上,该来的都会来。喜剧性的死而复活的心理,解释了作家的冷漠与温情的整体联系。绝对一点讲,余华的小说创作心理对悲剧是有所抑制的,因为悲剧是在一个更包容的喜剧阅读框架中进行的,悲剧的本质所要求的完整性被解构,荒诞的感受弥漫其间。正如诺思·罗普弗赖伊指出的那样:“悲剧实际是隐含的未完结的喜剧——喜剧本身之内包容着一个悲剧。”⑤也因此,像围绕福贵、许三观这样起起伏伏、劫难不断而又能够活下去的整体故事形态,充满“喜剧性仪礼”:“死与再生、生殖仪礼和种子的喻义。其模式是:考验,奋斗与失败,最终的胜利。”⑥“最普遍的喜剧模式看来是死而复活。”⑦余华创造性地抒写人物生命的喜剧意识,并成功将其变成人物的本质属性。余华小说中喜剧性的死而复活的心理图式,不仅在小说的叙事情节、整体的节奏中见到,而且也体现在人物的呼吸与行动上,显示了人物生命的喜剧意识。“许玉兰门槛哭泣”就是被人津津乐道的片段,许玉兰的哭泣,在看似委屈的抗争里将人物压抑的羞耻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前世造的什么孽?我一没有守寡,二没有改嫁,三没有偷汉,可他们说我三个儿子有两个爹,我前世造的什么孽?我三个儿子明明只有一个爹,他们偏说有两个爹。我前世造的什么孽?我一没有守寡,二没有改嫁,三没有偷汉,我生了三个儿子,我前世造的什么孽?让我今世认识了何小勇,这个何小勇啊,他倒好,什么事都没有,我可怎么办啊?这一乐越长越像他,就那么一次,后来我再也没有答应,就那么一次,一乐就越长越像他。一场一场的哭泣,从失衡到平衡,从情绪倾覆的酣畅淋漓到回归日常的平静,这就是底层人物死而复活的心理机制。许玉兰是如此,福贵是如此,许三观也是如此。就是这样,余华总是将悲剧的内容置放在更开放的喜剧性的审美阅读框架中,表现人物在情境中的活动。⑧其次,通过象征“呕吐物”“排泄物”的内容呈现,人物在狂放的喜剧行为中释放压抑的情绪,叙述者也获得一种相对紧张的释放。上述“许玉兰门槛哭泣”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许玉兰的话语象征底层人物的“呕吐物”,那些粘附在卑贱者身心上的污渍应当被清除掉,这是卑贱者的权利以及继续活着的应对方式。对于作为类型的底层来说,在象征的意义上,余华小说中“呕吐物”“排泄物”的典型形态就是死亡。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从一开始就把生存境遇中的杀戮、死亡视为底层生存的“呕吐物”“排泄物”来处理。在《现实一种》中,无论是皮皮的死亡还是山岗对山峰实施的异想天开的残酷刑罚,都可以视作这个底层的令人憎恶的“呕吐物”“排泄物”。这样的书写,因底层缺乏自身历史、小说人物身份构成的背景以及来路的叙述,因而很难有一个指涉历史或现实的主体要为此负责。因此,这个底层就像一个横行的无头庞然大物,其“呕吐物”“排泄物”又可不断感染传播。《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们读到“我”的父亲孙广财和“我的哥哥”同睡一个寡妇以及孙广财对自己父亲孙有元往死亡结局的推送,都是这个底层令人憎恶的“呕吐物”“排泄物”。因为缺乏相应的主体归附,没有自我的反省和思考,相关的羞耻就在小说中漂浮,却没有可以入住的主体。纵然有羞耻的感受陈列在那里,也是无从认领的东西,无从认领的羞耻是谁人的羞耻?在《细雨中呼喊》中,当孙广财喝醉了酒掉进粪坑淹死后,“浮起来像一只猪”——小说以讽刺的、夸张的描写将死亡象征的事物给予否定和清除,从而使生活得以向前挪动。同时,应该指出,不是只有悲剧才涉及宣泄。作家对世界以喜剧的方式加以把握,同样能将世界与人的紧张关系、人物的焦虑进行释放。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者,既然是故事的讲述者,则必须体验底层卑贱者的宣泄,共同的体认在于清除、清空后的状态可使或简单或清爽的生命状态平静下来。在余华小说的喜剧性中,我们体会到一种紧张突然得到释放,体会到书中压抑解除后的紧张搁置,体会到在绵绵不绝的死亡的缺口中挣脱出来的轻松,体会到书中人物在经历磨难后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时,直接面向读者交流的幽默(许三观在一次一次卖血后,血站不再认可他的血,他的儿子们也已长大不再需要他的卖血)……甚至,我们在《第七天》结尾处读到的那句“死无葬身之地”,也许能体会到些许黑色幽默的意味,在小说深陷的困境中逃逸出一点解脱的气息。此外,卑贱的、羞愧的甚至羞耻的体验与存在,在喜剧性的行为中既彰显又被防御地遮掩过去,在肯定生命存活的形态中消解着不适与尴尬。许玉兰的哭泣把一般人小心翼翼掩藏的羞耻公开化,她不再为这样的羞耻受罪,似乎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羞耻交付出去,同时又把这份羞耻变成一种保护自我的武器,理直气壮地责问命运的戏弄。在较低或更低的程度上,以活着为由,余华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这种避过自我的不适与尴尬的能力,在这些“光明的”小说中,这些不适与尴尬也许是生命可以承受之重?三、羞愧在别处:对作家的认读
与对许玉兰的提问相似,我们还可以从《活着》的阅读中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活着》中,看不到福贵因赌博输光了田产而有所羞愧(余华对这种变化安排为因祸得福——后来逃过了阶级成分划分的惩罚)?福贵底层身份的社会构成,因人物命运的拐点以及人物此后开展的人生都已经和羞愧无涉——除非如有的读者会认为仅仅像福贵那样活着会有羞愧的感觉。如果一个作家在写作人物时,对人物应羞愧的事情不以为意,并不能说明作家忽略了自己关于羞愧的观念。他可能在考验自己的耐心,或者出于其他某种考虑。例如,当羞愧因自我的内耗而不利于个体或者类群的生存时,驱除羞愧就成为一种必然。让我们记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余华表述他是为底层写作,但他也倾向于表达人都是一样的观点。如《活着》广为流传,最大限度地吸引着包括世界各地的读者(可以预见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不妨说,历经劫难存活下来而不必羞愧是引起共鸣的一个重要看点,至于在屡屡受挫的人生中所需要的勇气和通达也与此相关。余华的创作,历时三十多年,时间跨越了新旧世纪。这期间,中国当代社会发生的巨变之一,就是城乡的界限不断瓦解,乡村向东南沿海城市、偏远城镇向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动与迁徙,如贴近大地的一管管血液,参与维护着新兴城市、中心城市的亮丽面容。对那些在乡村的荒僻中劳作以及向城市移动中讨生活的漂泊者,余华习惯性地称呼他们为“底层人”(这样的称呼也许不够准确,有道德预判之嫌,不如说“打工者”更为客观)。从《第七天》追溯回去,余华的底层是从农村、乡镇走向城市的,所写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对于余华创作阶段性的作家精神特征,学界已多有描述,如对人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