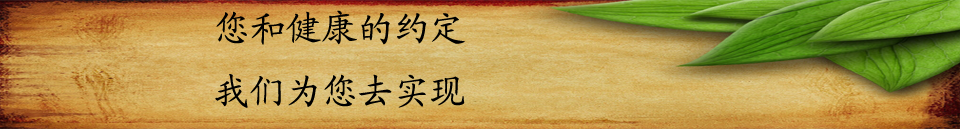
手淫Me,Myself,andI
性作为一种隐秘而又被禁止公开言说之物,总是同时处于欲望的冲动和道德的规训、私下的探索和公开的禁止之中。不过偶尔拿出来作为科普读物来看,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手淫(Me,Myself,andI)
ByStephenGreenblatt
译者:rhizome
1.两年前,我在哈佛主持“历史与文学”专业的时候,想出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错的主意。我们发起了一个定期举办的讲座,主讲人都是些以跨学科研究见长的著名访问学者。我以前伯克利的同事和朋友ThomasLaqueur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充满野心的新书,其中涉及医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神学和文学。
邀请Laqueur并非仅仅出于私人交情,他年写成的MakingSex如今已成名著——该书讨论了性别的医学发现或发明——并对从科学史、社会性别研究到文学批评和艺术史的一系列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现还是发明:Laqueur的主题是,性别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经验研究带来的,而是来源于一场复杂的社会价值重估。他指出,人们的性意识在十七、十八世纪中从单一性别模式转变为两性模式,女人的身体从前被认为只是天意造成的男人的残次版本,后来,人们开始认为两性器官是截然不同的了。也就说,人们放弃了过去古老的观念,不再认为阴道只是没能长出的阴茎,卵巢也不是得了隐睾症的睾丸。在文学领域,莎士比亚的假小子们(Rosalind和Viola)也被狄更斯那些奇怪的天使般的形象(AgnesWicklow或者小杜丽)所代替,后者看起来和男性如此的不同,仿佛以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来自不同的星球,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着不同的内部构造。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
Laqueur的新书《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与前述著作有着同样让人吃惊的主题:那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似乎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段“历史”,一段引人遐思、充满波折同时意义重大的历史书写。因此不难理解,在我看来Laqueur是讲座的合适人选,他的到来应该能让这个学期充满活力。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之前也发生了点怪事:系里爆发了一场恐慌。恐慌的并非学生,许多学生是看着电影《情迷索玛丽》长大的;恐慌的是教师中的核心成员:主持研讨班和课后辅导的那些人。他们成熟且受过极好的教育,可是他们都惧怕与学生讨论手淫的历史。食屎癖不会令他们感到困扰,肛交不会让他们退缩,乱伦甚至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主题,但是手淫:饶了我吧,别的都行。
私下讨论过几次之后,我召集了一次员工会议商议如何应对“手淫事件”。开会时,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在一夜之间变得对双关语超级敏感,就仿佛语言本身出了问题。“Laqueur什么时候来?”窃笑。“他的讲座出了点问题。”咯咯笑。“我们希望商量出什么结果呢?”哼哼声。“如果他的到来让大家不爽,我很遗憾。”爆笑。也许是想对这种集体的愚蠢作出反应,一位经验丰富、通常表现得很明智的教师站起来发表了一通急切的演说。“我以前也教过和性有关的课程”,她严肃地说道,“讲这种课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决不能把幽默扯进来。一旦你让学生笑起来,一切都完了。”
鉴于手淫一事很容易引起笑声,当时的场面已经够古怪了,但更古怪的是另一名教师的反应。他宣布,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让学生阅读Laqueur的新书或者听他的讲座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尽管他承认,讨论人类行为的医学化与想象力二者的关系并非不重要,但这一讨论应该在他所谓“非强制性的框架”下进行,在这一点上,手淫是独特的。为了避免伤害他的良心,我免除了他的授课任务,并且告诉他,如果学生中有人和他持相同立场,他可以从Laqueur早些时候出版的另一本书里选择内容向这些学生传授,那本同样优秀的著作说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日学校和工人阶级文化。这样的学生一个也没出现。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新闻周刊》一个咯咯笑的记者打来的电话,她听说了我们的讲座。“好极了,”我说,“我很高兴你来写写我们这学期的讲座。”不,不,她答道,她只对那个讲座感兴趣。明白了她的意思之后,我以一种警惕的冷静对她说,原来你对十八世纪的的疾病分类学感兴趣。她听上去很失望。这本杂志最后只是在某个角落提了一句:“现代手淫大师”来哈佛了。
这时我才充分意识到,Laqueur触及了一个既怪异又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会没有预见到?难道我没读过PortnoysComplaint(PhilipRoth的小说),没看过《宋飞外传》(美剧)?上届政府炒掉了公共卫生局局长JocelynElders,就是因为她公开支持手淫。在迈阿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说,Elders对此事的态度反映了她本人“与政府政策及我个人意见的分歧”。手淫在各种普遍的人类行为中显得如此独特,它引起了一种特别的,而且特别强烈的焦虑。
Laqueur发现,这种焦虑并非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并且并未见于我们自己文化的遥远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手淫最多带来短暂的难堪或者嘲笑,但它很少或完全不具备医学上的重要性,就我们所知而言,亦不具备文化上的重要性。更令人吃惊的是,Laqueur指出,在古犹太人的思想中这种焦虑也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乍看上去并不可信,因为《旧约·创世纪》第三十八章里我们读到了俄南(Onan)“遗精在地”,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Onanism的确变成了手淫的同义语,但是创作《塔木德》和米德拉西(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讲解布道书)的拉比们却并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俄南的罪并不在手淫,而在于故意拒绝生育。在他们的范畴——生育,崇拜,污染等等之中,沉溺于自力更生带来的性快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Eliezer拉比写道:握着阴茎小便的人就如同把洪水带给世界。有些注释者对此言论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是在谴责手淫带来的快感,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注释者关心的也只是对精液的浪费。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的确对作为一宗罪的手淫有更清晰的概念,但是,Laqueur称,神学家们对这种罪并没有特别的兴趣。除了五世纪的修士JohnCassian之外,其他人关心的都是Laqueur所说的社会性的性行为伦理、而不是个体的性行为伦理。最重要的是“作为变态社会生活的性变态,而不是远离社会的、自足型的性变态”。在修道院里,令人紧张的是僧侣的鸡奸行为,而不是手淫,而在世俗世界,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中科UM-D

